2025 年 9 月 6 日,著名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因癌症相关并发症去世,享年 87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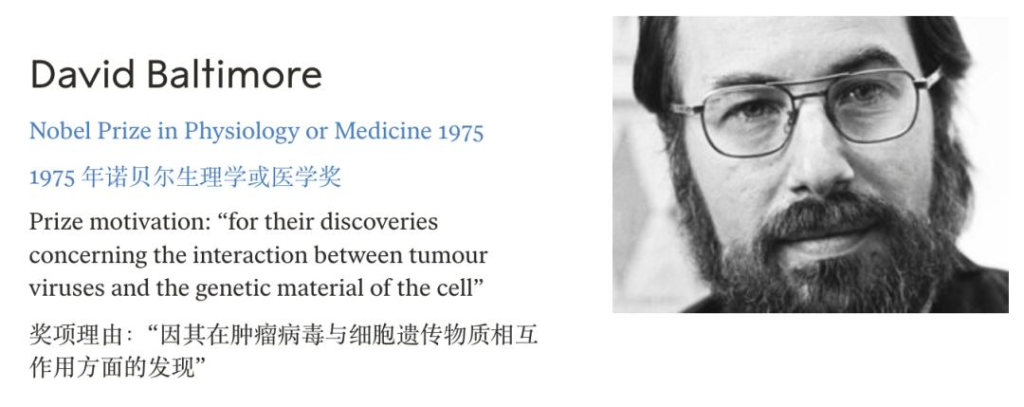
大卫・巴尔的摩,生于 1938 年 3 月 7 日,32 岁时,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 逆转录酶 ,这一发现颠覆了 “中心法则” 描述的细胞中遗传信息流动方向 ——DNA 到 RNA 再到 蛋白质。在逆转录病毒中遗传信息能够反向流动 —— 逆转录酶能够将 RNA 反转录为 DNA。这一发现为他赢得了 1975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逆转录酶的发现,对 “中心法则” 做出了重要补充,促进了我们对逆转录病毒(包括 HIV 病毒在内)的理解。此外,大卫・巴尔的摩 还在免疫学、病毒学、癌症、重组 DNA 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除了科研成就,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大学管理者,曾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创建了 Whitehead 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的实验室培养了许多博士和博士后,其中许多人后来取得了杰出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2025 年 9 月 4 日,国产学术期刊 Immunity & Inflammation 上线了首批 4 篇文章中,包括大卫・巴尔的摩作为通讯作者的综述论文,全面综述了 NF-κB 在调控免疫反应、炎症、细胞存活、增殖和发育中的功能和潜在机制。NF-κB 是大卫・巴尔的摩除逆转录酶外最重要的发现。
《纽约时报》在给大卫・巴尔的摩的讣告中写道 —— 大卫・巴尔的摩备受敬仰又遭人嫉妒,备受推崇又饱受攻击,他的一生都处于科学界的聚光灯下,他是现代生物学领域的一位巨擘。
高中时期对生物学产生兴趣,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1938 年 3 月 7 日,大卫・巴尔的摩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他在高中时期因参加杰克森实验室 的暑期学生项目而对生物学产生兴趣,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霍华德・特明 (Howard Temin),他们后来一起获得诺贝尔奖。
1959 年,大三期间,大卫・巴尔的摩作为首届本科生研究计划成员在冷泉港实验室 度过了一个夏天,由此接触了分子生物学,并在这里了结识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Salvador Luria(噬菌体研究先驱,1969 年诺贝尔奖得主)和 Cyrus Levinthal (蛋白质折叠研究先驱),他们正在为一个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生教育项目挑选候选人。1960 年,大卫・巴尔的摩 以优异的成绩从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两人的邀请下,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但他早期对噬菌体(细菌病毒)的兴趣很快转向了对动物病毒的热爱。
1961 年,大卫・巴尔的摩参加了冷泉港实验室的动物病毒学课程,并选择前往洛克菲勒大学 完成其关于动物病毒学的博士研究。在洛克菲勒大学,他做出了关于病毒复制及其对细胞代谢影响的基础性发现,包括首次描述了 RNA 复制酶,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于 1963 年(25 岁)获得博士学位。
1963 年,大卫・巴尔的摩 回到麻省理工学院 (MIT)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继续利用脊髓灰质炎病毒开展病毒复制方面的研究,并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接受了酶学方面的培训。
1965 年,年仅 27 岁的大卫・巴尔的摩接受 Renato Dulbecco(他们在 1975 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邀请,在新成立的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e)担任独立研究员,在此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 RNA 的复制。1967 年,他在索尔克研究所结识了未来的妻子 —— 黄诗厚 (Alice Huang) 。在此期间,大卫・巴尔的摩做出了一项重要发现 —— 脊髓灰质炎病毒将其蛋白质作为一个大的多聚蛋白产生,随后再被加工成单独的功能性多肽。
1968 年,大卫・巴尔的摩再次受 Salvador Luria (1969 年诺贝尔奖得主)邀请加入 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微生物学副教授,黄诗厚也来到 MIT 继续研究水疱性口炎病毒(VSV)。几个月后,他们二人成婚。在 MIT 工作期间,他们一起发现了 VSV 的复制涉及病毒颗粒内的 RNA 依赖的 RNA 聚合酶,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策略来复制其 RNA 基因组,VSV 以单链负链 RNA 的形式进入宿主细胞,但携带有 RNA 聚合酶,以刺激 RNA 的转录和复制过程。
发现逆转录酶,颠覆 “中心法则”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大卫・巴尔的摩进一步研究了两种 RNA 病毒 —— 劳斯鼠白血病病毒和劳斯肉瘤病毒,进而发现了逆转录酶 (Reverse Transcriptase)—— 这种酶能以 RNA 为模板合成 DNA。通过这一发现,他找到了一类独特的病毒 —— 逆转录病毒 ,这类病毒利用 RNA 模板催化合成病毒 DNA。这一发现颠覆了 “中心法则”,中心法则认为,遗传信息是从 DNA 单向流向 RNA 再流向蛋白质,而逆转录酶和逆转录病毒的发现,表明了遗传信息可以在 DNA 和 RNA 之间双向流动,从而对 “中心法则” 做出了重要补充。
1972 年,年仅 34 岁的大卫・巴尔的摩成为 麻省理工学院(MIT)终身教授。1974 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975 年,年仅 37 岁的大卫・巴尔的摩 与 Howard Temin 和 Renato Dulbecco 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词写道 —— 表彰他们在肿瘤病毒与细胞遗传物质相互作用方面的发现。其中,大卫・巴尔的摩 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逆转录酶,这类酶对于诸如 HIV 等逆转录病毒的繁殖至关重要。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大卫・巴尔的摩重组了自己的实验室,重新将重点放在免疫学 和 病毒学上,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
1982 年,大卫・巴尔的摩 接受捐款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创立了 Whitehead 研究所 ,在他的领导下,Whitehead 研究所创立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了全球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顶尖研究机构。
1986 年,大卫・巴尔的摩发现了一个关键转录因子 ——NF-κB,其在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以及病毒调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引发了 “信息爆炸”,成为了过去几十年中研究最为深入的信号转导范例之一。
1988 年和 1989 年,大卫・巴尔的摩发现了重组激活基因(RAG)编码的 RAG-1 和 RAG-2 蛋白是介导免疫球蛋白和 T 细胞受体基因重排的核心重组酶,这一发现对于确定免疫系统如何在众多可能性中对特定分子具有特异性至关重要。这被大卫・巴尔的摩 认为这是自己在免疫学领域的最重要发现。
1990 年,大卫・巴尔的摩发现并证明了一种名为 BCR-ABL 的融合蛋白足以刺激细胞生长并引发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这一发现为后来著名的抗癌药物伊马替尼 (格列卫)奠定了基础,该药物通过抑制 BCR-ABL 蛋白,在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方面具有显著成效,还在治疗胃肠道间质瘤(GIST)方面显示出希望。
1990 年,大卫・巴尔的摩 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大学 的第六任校长,但仅仅一年半后,他因涉及 Thereza Imanishi-Kari 的学术不端指控而辞任校长职务。1994 年,大卫・巴尔的摩 重返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
1996 年,上述学术不端指控被裁定为毫无根据,
2019 年关闭实验室,上周仍在发表论文
2005 年,大卫・巴尔的摩从加州理工学院校长职位退休,但仍然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生物学教授和密立根讲席教授,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2019 年,81 岁的大卫・巴尔的摩决定关闭实验室,正式退休,为年轻科学家腾出更多发展空间。他表示,“我从事科研工作 60 年了,是时候把这个领域交给年轻人了。”
巴尔的摩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许多其他职业的人都爱说‘TGIF——Thank God it’ s Friday’(感谢上帝,今天是周五)。我能够代表我共事过的大部分科学家说,我们并不把科研当成一份工作,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机会穷尽一生去探索人类知识的前沿,那是一种上天的赏赐。”
即使在退休之后,巴尔的摩仍然关注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并继续参与一些学术活动。令人惊叹的是,就在他去世前一周,2025 年 9 月 4 日,他作为通讯作者在国产学术期刊 Immunity & Inflammation 上发表了一篇综述论文,题为 “NF-κB: Master regulator of cellular responses in health and disease”,全面综述了 NF-κB 在调控免疫反应、炎症、细胞存活、增殖和发育中的功能和潜在机制。NF-κB 是他除逆转录酶外最重要的发现。
纵观大卫・巴尔的摩的一生,他在科研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教育和科研管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的科研成果不仅推动了生物学领域的发展,也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坚持、热情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激励着无数后来的科研工作者不断探索未知,勇攀科学高峰。如今,他的离去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将永远铭刻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